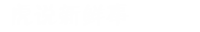白鹿原
一晃就是两年多。2011年7月21日,我打电话给陈老师,说想去拜访,陈老师说他家中有事,等几天再见,要我将手机号码给他发过去。三个月后的10月22日,他打来电话,说最近有空,可以一见。我问次日可否,他说可以。次日,下起了小雨。一大早,我到石油大学北门,在门口买了一条长城牌细支雪茄、一箱奶,还有一些水果,直奔他的工作室。2003年开春,陈老师从西蒋村老屋回到西安,一直在这里工作见客,直到病重住院。工作室在一幢上世纪90年代修建的旧楼上,同周围簇新的高层比起来,显得颇为陈旧和沧桑。门铃上的数字已漫漶不清,需要按照排列顺序来推测。反应也很迟钝,按了好久,才听到陈老师的声音。上到三层,防盗门已经推开。我喊了一声陈老师,他连声说:“进来,进来!”踏进屋内,陈老师从沙发上起身,说:“来就行了,带东西干啥?”我说这是晚辈见长辈的礼节,笑着将手中的东西放下。他招呼我坐下,拿纸杯,打开茶叶罐,用长柄的小木勺舀茶叶。我们平时招呼客人,都是用手捏茶叶,由此可见,陈老师是个心很细的人。给我留下难忘印象的还有他的灰蓝色的已经泛白的秋裤。这种秋裤,在《白鹿原》出版的90年代,我也曾穿过,那已是近二十年前了,此时已经很少见。
陈先生在书房里
一种很复杂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:我不知道他是简朴还是恋旧,竟然还穿着早已淘汰了的旧物。我打量室内,客厅很小,是过去的两室一厅,大概五六十个平方。房门对面,是一条长沙发,上面和靠背上堆满了书籍杂志,剩余的空间,也就一个人能够坐下。茶几上香烟、卷烟和茶叶散乱地摆放着,烟灰缸的凹口上,搁着半截熄灭的雪茄。电视声音很小,正播着球赛。泡好茶,他在对面的沙发上坐了下来,点燃了那半截雪茄,开始聊了起来。他聊发表不久的短篇《李十三推磨》,讲到自己上高中时推磨的经历,很投入,我尽量跟着他的讲述,想象推石磨子的情景,不过那种辛苦却难以感同身受。他说自己最近打算写王鼎的小说,但材料太少,还在准备。聊到十二点多,我邀他一起吃饭,他说中午要午休,一般不同人吃饭。临走,他问有没有雷达点评的《白鹿原》,我说没,他说那送你一本,拿书,签名,盖章。我们一同出家属区门,他到学校食堂吃饭。
之后,每隔一段时间,我就问陈老师。有时我打电话,问候我的身体状况,交流关于文坛的信息;有时朋友来拜访,我会带着他们。有时候我带朋友同学去找他签名,或者拿到字;有时候我也会给他我自己的文章或者和他相关的评论。2011年底,我写了一些关于他的老式诗给他看。他很高兴,说如果我愿意,他可以把它们送到某个地方。我觉得不成熟,就说先放一边,然后再改,以后再发。这么说,后来确实做了修改,但是他死后,这些老套的诗还是没有出来,他也没有看到。我喜欢去拜访他。他对生活、文学、社会的自由闲言碎语,是伴随着自己的经历和理解而来的,这是书本上学不到的。这种闲言碎语,当然涉及到对文坛内幕的揭露和对一些作家作品的评价,有些是大多数人闻所未闻的。有一次,他谈到80年代末90年代,北京的丛、都想当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。但副理事长的选拔要考虑地域平衡、各种风格的平衡、性别、民族等因素,副理事长不可能集中在北京,所以没有被任命是很遗憾的。他还问我如何评价一些作家,谈论他感兴趣或熟悉的东西,他的见解,他的敏锐总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他不回避对一些作家的厌恶。例如,一个作家曾经因为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而失去理智。一个作家睁着眼睛撒谎。当一个作家打电话给他时,他的头变大了...除了岳丹这个人物,他也认可自己的作品。他记得、刘、张炜、王蒙、刘震云、丛、张贤亮、雷、等人的作品,他都讲客观独到的见解。他还提醒我写评论要尽量客观,说我批评了一些得过毛奖的作品,有点苛刻。我真诚地接受了,感谢他提醒我以后会注意。
推荐阅读
- 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 历史上真实的陈世美 陈世美为何成负心汉代表
- 陈耀兴图片 连载28年的《古惑仔》完结 热血少年们早就老了
- 陈小春和他孩子的综艺 陈小春要保护儿子隐私却带他上新综艺 看到处理方案后 全网纷纷点赞
- 牛犇是什么意思 演配角、住老年公寓的影帝 85岁的牛犇:让陈道明屈膝弯腰
- 韶音 专访韶音创始人陈皞:骨传导技术 未来发展不输TWS
- 麻一鸣 你所知道的陈薇还有另外一面
- 陈志朋 吴奇隆50岁 青春散场
- 陈皮鸭腿怎么做才好吃?冷水里面投凉,这样会让鸭肉更加的紧致
- 陈洪国 简阳市司法局 举办《民法典》·开讲啦第二期专题培训会
- 陈金财 他是八极拳宗师,也是溥仪最信任的保镖,他的名字叫霍殿阁